根敦群培的弟子及施主霍康·索朗边巴,以及撰写《喇嘛王国的覆灭》的戈尔斯坦教授均认为,在被捕前,根敦群培已经开始撰写《白史》。他给这本书起名《白史》,正是为了表明不偏袒宁玛、萨迦、噶举、格鲁任何一个教派,完全出自公平之心。根敦群培1945年回到拉萨之后,迅速开始撰写《白史》,正是感受到一部真正西藏史的急迫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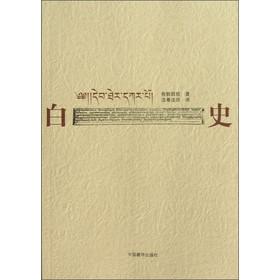
《白史》封面
“蕃“字从何而来?
《白史》撰写了仅仅几十页,刚刚写完松赞干布,尚未开始赤松德赞时代,根敦群培即被捕入狱,遭到极大摧残,直至去世也未完成。《白史》可以说是一部残卷,然而正是这部仅有几十页的残卷,让根敦群培被誉为“从神史转向人史”的第一人,是现代藏学的开山人物,是杰出的史学家。究竟是什么让《白史》如此特别,我们可以结合另外一本对西藏有深远影响的著名史书来综合阅读,这就是《西藏王统记》,成书于明代洪武年间,作者是萨迦寺座主、宗喀巴的上师之一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据刘立千译订本,《白史》据格桑曲批译本)
在《西藏王统记》中,开宗明义地说明本书的写作目的是,将松赞干布及相继出世之法王祖孙数代大兴佛教的史事“广为流布”。因此,《西藏王统记》开篇用了六章来诉说释迦牟尼世系等宗教内容。而《白史》一上来就指出其是一部世俗的而非宗教的历史。接下来,根敦群培更明确指出,他所参考的资料主要来自敦煌出土的吐蕃文书,以及《唐书》等汉文史籍。
在开篇部分,根敦群培完全没有提宗教,而是考证了几个根本性的问题:吐蕃的“蕃”字,也即藏民族的自称,究竟从何而来?吐蕃王族以及大臣的名号、服色究竟是怎样的?应当以何种纪年方式为准?这些问题在以往的宗教性史书中一概是忽视的,有学者主张西藏最初的王族是印度来的王子,顺水而下被冲到西藏。《西藏王统记》记录的则是猕猴和罗刹女结合生出藏族初民,天降赞普的传奇故事。对于前者,根敦群培是坚决反对的,他用自己异常辛辣的语言指出:“众所周知,世中哪有一条自印度倒流入西藏的河流?连如此最起码的常识都不具备,还将那些无端异说当作确凿证据吓唬我们。”(《印度北部的雪山及有关问题的辨析》)。
因此,关于藏族的起源,根敦群培丝毫没有提及“猿猴化人”这个颇有神话色彩的故事,而是大段地引用《新唐书》、《旧唐书》中对于吐蕃先祖的记载,此外辅佐以《国王遗教》、《巴协》等古书中对吐蕃古风的记录。
蕃一词的辨析有重大的意义,事实上构成整个西藏史书的根基,根敦群培大胆指出“蕃”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原始词,或者是将王名当作了地名。他还放下门派之见,提出了苯教徒的看法,即“蕃”来自“苯”,并且认为“这个观点也值得略加思考”。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此事“不问两千岁的老者,有谁能够了知?”承认对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而不是先入为主,从宗教中寻找答案,这恰恰体现了根敦群培实事求是的修史风格。实际上,直至今日,藏学界对于“蕃”字的来源依然没有达成一致。
松赞干布是否盛年而卒?
《西藏王统记》用了大量笔墨描写了被西藏人民尊为“观音菩萨化身”的松赞干布时期创立文字、迎娶尺尊公主和文成公主,修建大小昭寺,并且于80多岁时功德圆满,同一日与尺尊公主、文成公主共同融入自然生成的十一面大悲观音像心间。其篇幅大约占了全书的二分之一。《白史》同样热烈地歌颂了松赞干布的丰功伟业,其着眼点却是不同的方面。《白史》中更为重要的贡献,或许是考证松赞干布的生卒年月。《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等经典史籍均认为松赞干布是80多岁时入灭的。一个树立如海般功业的赞普,观音菩萨的化身,自然应寿命长久。而《白史》通过《唐书》的可信纪年进行综合考证,得出了准确的松赞干布年谱:松赞干布13岁登基、25岁迎取文成公主,34岁时即英年早逝。他的死因,根敦群培根据苯教经典大胆猜测为被害。而且文成公主、尺尊公主也并未随他一同过世。根敦群培写道,敦煌吐蕃文书中有明确记载,文成公主在松赞干布死后,仍在世31年。
这一大胆的见解,如今已经成为藏学界的共识,但在当时,的确无疑是石破天惊般的大胆创见。然而根敦群培并不畏惧,他辛辣地写道:“总之,那些认为松赞享年80余岁的人,则必须面带微笑勉强承认藏王79岁高龄时,才娶唐朝公主为妻的。”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实事求是的无畏态度,他又说:“叙述通常的藏王历史时,应以人世间所发生的事故为主题,此时无需为特别显示藏王的盛德而增添种种离奇的传说。”正所谓“此乃自然真实月,现出无垢白螺色;何必只因偏执俗,绘出长耳丑兔形”。
消失的史料
根敦群培在《白史》中还有诸多创见:例如从石碑文字推断乌梅体是乌金体快写而成,而不是一般认为的分别由两种语言创制,考证吐蕃的服色,并推断地方神灵“赞”的服装和赞普服装类似等等;考证经幡柱原是吐蕃军队的长矛,后来逐渐成为信仰标识等,在此不作赘述。
根敦群培未能完成《白史》,实在是西藏史学研究的重大遗憾。据当事人目睹,他被捕时,要求给予的唯一优待是保存好他所做的关于西藏历史的笔记。“他的房间除了床上外,到处摆放着他的手稿。这些手稿全都分类排列,他不允许任何人接触它们。据说这是他从事敦煌古藏文手卷和西藏等地的碑铭研究多年的结晶。”
然而噶厦政府却不懂这些文献的重要,“检察官们毫不在意地将这些手稿和文献收在一起,然后将它们扔进一个黑色旅行箱。”
这些珍贵文献自此消失,不知去向。
关于我们 丨联系我们 丨集团招聘丨 法律声明 丨 隐私保护丨 服务协议丨 广告服务
中国西藏新闻网版权所有,未经协议授权,禁止建立镜像
制作单位:中国西藏新闻网丨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朵森格路36号丨邮政编码:850000
备案号:藏ICP备09000733号丨公安备案:54010202000003号 丨广电节目制作许可证:(藏)字第00002号丨 新闻许可证54120170001号丨网络视听许可证261059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