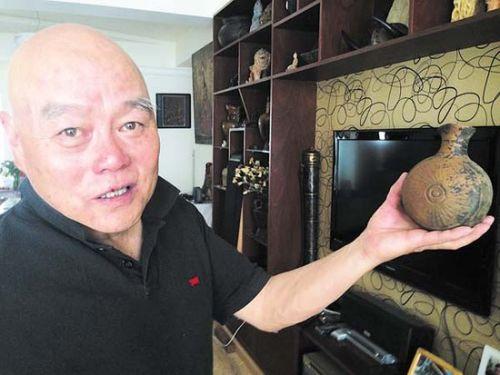
张鹰
我出生在陕西关中平原,父母是地道的农民,可我从小喜欢画画,中学时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要报考美术学院,文化大革命让我的梦想化为泡影。1968年初中毕业,我和千千万万个老三届一样,响应党的号召,返乡务农。那个年代虽说是一个荒废的年代,却也锻炼人。在农村,我的画画特长有了用武之地,画过毛主席像、阶级斗争宣传画、画过土电影(幻灯片)。我忘不了在蒲城县文化馆业余美术组学画的那段艰辛而又充实的日子,每个星期天骑自行车往返一百多里路,参加县文化馆每周末举办的美术辅导学习,现在看来,那算是我艺术人生中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深造,尽管是短暂的。我忘不了那一时期给予我关心和帮助的中学老师韦宏达、蒲城县文化馆的美术老师高起胜。
1972年初西安美术学院开始恢复招生,这是我期待多年的梦想,在众多考生中我的成绩名列前茅,可万万没想到,因为填表时我在婚姻状况一栏里老老实实写上了已婚,结果政审时被取消了。从此,美院梦跟我擦肩而过,我为之痛哭一场。时隔半年,西藏秦腔剧团来陕招生,其中要招一名舞台美术人员,这对我来说又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那时,对西藏我一无所知,只听说很远很远,可我不在乎,只要能有份画画的工作就行。我幸运地被录取了,当时别提有多高兴。可怎么也没想到这一步跨出,我就再也无法离开西藏。就这样,我舍下了年迈的父母和新婚的妻子来到了西藏。
我在上中学时就把父母给我取的名字春生改成了“鹰”,这正是冥冥之中我和西藏的一份情缘,西藏不正是鹰的故乡吗?命运把我带到了西藏,我本该属于西藏!
刚进藏时,我住在拉萨八廓街东南角一座古老的藏式庭院里,这里是西藏秦腔剧团所在地。后来才知道这座庭院原来是旧藏政府官员索康家的宅院,是当时八廓街里典型的藏式庭院之一,庭院的西面三层阁楼朝东,其余三面两层廊房环绕,中间是一个大的院子,院子中间有一口水井,除了我们这些住在院里的人,附近居民都从这口井里背水,大家的关系处得非常好,像一家人。我对西藏的了解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每天进出八廓街,耳濡目染着浓浓的藏域风情,至今都怀念那段难忘的经历,尽管那时生活条件很差。后来我之所以痴迷西藏的民俗风情,应该与最初在八廓街里的熏陶和感染分不开。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八廓街里环境很差,相比今天的八廓街可真是天壤之别。但那时的八廓街很淳然、很真实。走进八廓街里有种扑面而来的藏风、藏味。也许是我在八廓街里住久了的原因,对那里有了浓厚的感情,甚至当时八廓街里让人难以接受的气味在我认为也是拉萨特有的一种生活气息。虽然这辈子我跟大学无缘,可我从没后悔过,我和西藏的这份情缘是无法用任何一所大学来衡量和比拟的。西藏就是我的大学。刚进藏那些年里,我几乎天天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每天背着画夹或油画箱,不知疲倦地穿行在拉萨的大街小巷、城郊田园,甚至搭乘便车到数百公里以外的乡村、草原去写生,留下了数百幅油画、素描和速写作品。因为太喜欢画画,我很快把自己融入到西藏人的生活与文化中。
1983年,组织上调我到西藏藏剧团工作,这又是我艺术人生的一次大转折,也是我被带入藏文化领域的一个契机。从此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文化领域,藏戏中蕴含的西藏特色文化和艺术魅力深深地吸引了我,也彻底改变了我。我的审美观开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藏戏中我看到西藏传统文化的特性和人类根性文化的特征,我也从中找到了现代艺术与原始文化的契合点。1988年,我设计传统藏戏《白玛文巴》的舞台布景,正是利用古老藏戏中原始的表演形式与现代思维相结合,后来这个舞台设计应邀参加了1989年的“上海国际舞美艺术节”,用一个专家的话说,在当时国内这是一个设计理念超前的舞美艺术创作。正是因为对藏戏的理解转而对西藏传统文化的酷爱,我开始明白,发现美和创造美一样重要,西藏的美无处不在,我开始迷上摄影,用镜头记录西藏无处不在的美和那些美的创造者们。1986年,我担任《中国戏曲志·西藏戏卷》、《西藏音乐集成》图片编辑,更有机会到西藏各地采风拍摄,相机替代了手中的画笔,从此埋头于西藏民俗摄影。我永远忘不了和好友边多先生一起下乡的日子,我在藏文化方面的知识都是得自于他的传授,边多不仅是我多年的挚友也是我最敬重的老师。就这样,不经意间我又成了西藏名副其实的民俗摄影家。以至今天没多少人知道我会画画。其实,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摄影就是我画画之余的最爱,那时我拍照片目的是收集画画的素材,没曾想几十年后这些照片成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自2000年以来,我大多时间用在编书,先后出版了《西藏艺术》丛书、《西藏民间艺术》丛书、《人文西藏》丛书等。说来也惭愧,我说是初中毕业,不过是高小文化水平,记得刚到西藏时我写给中学老师的信,老师修改后又寄给我。所以过去除了想画好画我从没敢想过写文章编书,可没想到后来还真的出了一大堆书,用朋友的话说我这是积淀深厚,到时候自然溢出来了。我心里很清楚,这是西藏文化的感召力把我推上了浪尖,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需要。我在西藏的大文化中一步步长大,又一步步成熟。
因为热爱画画我来到西藏,后来因为爱上西藏就爱上了西藏文化,也就爱上了摄影;这就有了数以万计的图片积累。如果《人文西藏》丛书的出版对我来说是一种成功,也可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而每一次编书的过程都是我对藏文化认识上的一次升华。也许正是这些丰厚的积累和对藏文化深层的理解,我的画开始变了,变得热烈,变得深沉,变得厚重。我热爱自然、热爱生活,更热爱西藏民间文化。这样说来我多年的摄影、写文章编书并不算是弯路,而是我情感世界的铺垫,最后这种情感将归结到我的画中去,因为对我来说感情只能通过画笔来表达,画画才是我生命的灵魂。
转眼我到西藏就四十年了。我在西藏这近四十年的经历是多变的,也是充实的。我的性格决定了我的一生,干什么爱什么,钻研什么(也许是自学的原因),朋友常常介绍我时不知道该怎么说,是画家、摄影家、民俗学家,我笑答“杂家”。好友韩书力多次规劝“善取不如善舍”,我也曾下过决心,可对我来说舍去哪一块都好像割去我的心头肉,是西藏文化情结一直在纠结着我的心。现在书也出了不少,我的心开始回归到原初,回到画的世界。其实这么多年来我并没有完全放下过画笔,《酒歌》、《古道》、《耕》、《山村》、《远山》等三十多幅画,都是在我编书的过程忙里偷闲画的,多年来我习惯了杂乱的工作,反倒觉得很充实。一个人的成长不是孤立的,我在西藏几十年的进步与成长曾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都铭记在心。韩书力是我多年的挚友和老师,我们差不多同年进藏,又一起走到今天,用吴作人先生的话说,我们都是“嫁到”西藏的人,他对艺术的执着与追求一直影响着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我的油画写生正处入高潮时期,是陈丹青给我上了油画色彩宝贵的一课,他曾极力举荐我到中央美院进修,但都因为我当时工作不能脱身,单位不放,永成遗憾。我还忘不了余友心老师以及不少画界朋友的帮助。我更忘不了我的许许多多藏族朋友们,他们才是我永远的老师。
2011年正好是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周年,六十年来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有幸亲历了改革开放以来西藏迅速发展的三十多年。“四十年雪域情痕”正是四十年来我对西藏不解的一份情缘。画册按年代分为四个部分,也是我在不同时期对西藏的认识和理解,也寓意着西藏的进步与发展历程。为了增进作品的历史感和文化内涵,我为每幅作品配了相应的短文。我想,就我的画本身还显得不够成熟,但大多朴实,少一些张扬,这也许是我为人的风格。我只想通过这些画告诉人们,这就是我心目中真实的西藏。
(二)

说八廓街是西藏的窗口一点不假,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一头扎进这里,每天感受着八廓街的气息,目睹八廓街里的瞬息变化。应该说,西藏的变化最先从八廓街里人的变化开始。我刚到拉萨那几年,拉萨流动人很少,每天转经的多都是拉萨的老人,而且寥寥无几。1976年改革开放,八廓街里的人开始多起来,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八廓街里已是人潮如涌,他们多都是来自藏北和康区的牧民,所以满街看到的都是羊皮藏袍,有年迈的老人、有强健的康巴汉子、有纯情的牧民少女……他们的身上散发着只有大自然才拥有的那种原始美,他们的眼睛里流露着一种人本真的纯真与自然,还有那种充满雕塑感的紫铜色肌肤,这种感觉就像一种高强的磁石在紧紧的吸引着我。
进藏开始那几年我每天都泡在八廓街里,画素描、速写,油画写生。虽然我这一生没能上过任一所美术院校,但我却有幸在八廓街里泡了几年,这是上天赐予我的恩惠。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拉萨画画的人很少,有的是报社的美编,有的是剧团或展览馆等文化单位的美工,因着相同的爱好大家经常在一起互相切磋,互相学习。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对学习画画的渴望非常迫切。还记的我刚到拉萨时,西藏美术界有影响的老同志就数歌舞团的褚友韬和西藏日报社的马刚等,他们自然成了我时常拜访的老师。1973年,西藏日报上发表了我刚进藏不久随剧团支农收割时画的一幅速写《割青稞》,这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当时的高兴不亚于2010年我的油画《酒歌》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可以说,这两幅作品是代表了我的绘画生涯中两个不同时期的开端。
从1972年到西藏以后的那些年里,除了完成舞台设计制作,其余的时间我全用在写生上。应该说这十年是我西藏风情画创作的高潮。浓浓的藏域风情在感染着我。当时的拉萨很淳朴。从美术的角度,周围的人和景物呈现在一片灰色的基调中,恰是这种灰色给人一种幽静而神秘的感觉。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朝佛大军席卷拉萨,这座千年古城失却了往昔的幽静,但却平添了一种浑厚的壮观,那种壮观来源于一种厚重,是把各种颜色揉在一起的那种厚重。黑、红、黄、白、蓝浑然一体,既不沉重,也不跳跃。就这样,纯然的灰色基调成了我那一时期的创作风格。
作者简介
张鹰(1950.3—)陕西蒲城人。擅长油画。自学美术,先后在西藏秦剧团、豫剧团、藏剧团从事舞台美术设计,1983年调西藏民族艺术研究所从事美术编辑、西藏民间艺术研究。西藏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副研究员。作品有《高原之秋》、《鼓手》、《牦牛舞》、《风景写生》等。出版《西藏神舞、戏剧及面具艺术》、《西藏面具》、《西藏脱模泥塑》。编著《中国民间艺术全集·西藏卷》。主编《西藏民间艺术丛书》等。
关于我们 丨联系我们 丨集团招聘丨 法律声明 丨 隐私保护丨 服务协议丨 广告服务
中国西藏新闻网版权所有,未经协议授权,禁止建立镜像
制作单位:中国西藏新闻网丨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朵森格路36号丨邮政编码:850000
备案号:藏ICP备09000733号丨公安备案:54010202000003号 丨广电节目制作许可证:(藏)字第00002号丨 新闻许可证54120170001号丨网络视听许可证2610590号
